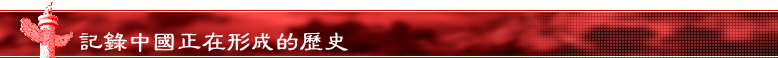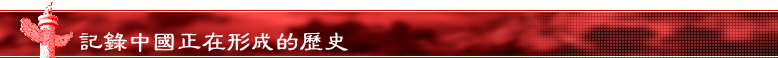|
ȫ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�f��ˎ��߀�ǽ������Ӻͽ���Σ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Ҋ��Ҋ�ǵ�Ԓ�}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ǚg��߀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ǰ�о���Ԓ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һ�w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㲻�������o·���ӣ�ֻ��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֖|�S�ֽ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һ���}�顰�߽���ȫ��֮·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ęC���c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ć��H�W�g��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вſ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@�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Ľ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"�ĺ��⽛���W�ˣ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Ć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ҕ���c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cҲ�S�y��ƫ�������sֵ���P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Ը����
ȫ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CĪ�e�^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罛��ȫ�Ěvʷ�^�̺ͻ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IJ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ʷ���ں鳯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֞顰��֪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X���͡���֪���X���Ĵ��
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֪���X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܄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ȏ������Ҍ��Ј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½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ĺ�Ň��ز��㣬�ɞ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Σ�C��һ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
Ŀǰ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ڡ���֪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Jͬȫ�������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ȫ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ȫ��λ���Ƅӷǽ����I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LjԳ֡����w���á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°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鳯�x�J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ٿ��Խo�Ї��ṩ�Ĵ�ʾ��
혣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o�ԁ����M��ȫ�İ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Ј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Ϣһ�w����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ʼ�K��׃���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ԈԳ��Լ��ărֵ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Ԍ��˲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Ԓ���o�^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Ԛ�ʽ���ۮ�܇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ڰ��˵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ܳɞ鲻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Ѕ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ܜp��ȫ��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ؓ��Ӱ�����
ȫ�����o֮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Ј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Ј���ȫ��ȻҪ����Ϣȫ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ɺͽ������ɾͳɞ��}�Б���֮�x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Ҫ����ȫ��`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ȫ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Ї��F(xi��n)�еķ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H��܉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ɡ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Ј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Ĺ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Ј������а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ԛ]�������İ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С����Юa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Ј������О鲻���ܵõ�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£��Ї���횄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ĸ߿Ƽ��aƷ���Էdz��ֶ��_���Ј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Ј�������ռ�I�Ј������Էdz���ʩ�_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Ą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Й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
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ɱ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o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ڌ�ʧ�C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һ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ǧ�d�y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Ҫ�Թ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Ј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ą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Ϣ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ȫ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О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λ���Ƅ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"��l(f��)�ӄ�"
���S����齛���ĸ��Mչ��һ���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ʹ�î�ǰ�S�ཛ���W�ұ��κΕr���Pע���θĸ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Ī�{ʲ��W����ϵ�v�����ڗ�С�P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ֻ�Ǒ����ĸ��һ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رܽ����ĸ��c�����ĸ�֮�g���P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õ��ġ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(y��u)�ݡ���K���ɞ顰��l(f��)�ӄݡ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˂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(y��u)�ݡ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ć��ҿ���ͨ�^�W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ҵij��켼�g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ߏ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˼���ʸߡ����@���ں��M�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¡�
����С�P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ć��ҿ���ģ�°l(f��)�_���ҵļ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ڃ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@�����L��Ч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µĝ����ѽ��ıM������߄ڄӷֹ��ľW�j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Ե��L�ڴ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H�I�ȵ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D�ͫ@�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顰�@�N�w�ƛ]�������ƶ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ƶȻ��A�O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С�P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ʮ����;�ʮ������˲�Ŀ�����L��Ч��Ҫ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l(f��)չˮƽ��ģ���µij��ڌ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ģ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С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Ј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ɖ|�������֙�͇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°l(f��)չģ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Ј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m����Ј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Ӌ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y(t��ng)һ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ģ���ϵ��Y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ģʽ��˹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Ҳ��ͬ�ڲ���Ч�κ��Y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ë�ɖ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
��С�P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g��ģ���Լ��ɴˎ����Ķ̕����s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ȵ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ģ�µĝ����ıM�Ժ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Ǒ���Ҏ(gu��)�t�D܉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܉���ٶȺ͕r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ƄәC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Σ����܌������ƶȻ��ć��ҙC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A�ӵļٹ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ǰ�ͺ��^�����
��С�P�Q�Լ����о��ǡ��dz����g�͡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رܬF(xi��n)���Ć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t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ߺͅ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ĽM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ƶȻ��ˇ��ҙC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ҙC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M����Ҫ�ИI(y��)�Ŀ��Ɓ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S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µ��И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И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y�ИI(y��)�]������Ř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F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칤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桢���l(f��)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С�P�Q������WTO�Ժ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c���HҎ(gu��)�t�����ڵ��ƶ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đ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H��܉���@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ı�Ҫ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2001��12��17��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