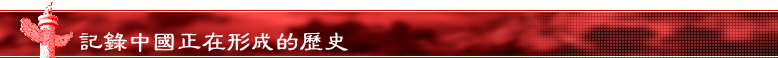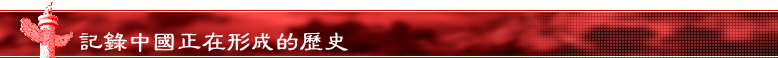|
�h��ʮ����ٴ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˼�룬ͻ�����ڇ�����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ϵK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W�Һ͌��Ҽ����ڈ��ϰ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»�Մ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Ķ�N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ʽ���˿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Մ���ˇ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w�ļ��g�Ԇ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ǣ��҂��Č��҂����]�лش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P�ĵĆ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㹫���ƵĶ�N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ʽ��ij�N�̶�����ζ��ȫ��ؔ�a���ٽM�������ٷ�������漰ȫ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档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Ƿ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廨���T�Ĺ����ƌ��F(xi��n)��ʽ���f�ø����_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w�����ʮ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ć����Y�a�Ƿ��ͨ�^�@Щ��ʽ����ƽ�ش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u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@����o�ɷ��h���P�I���҂��F(xi��n)�е��w���ܷ��C�@Щ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Թ�ƽ�ă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A���u�o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η�ֹ���е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ؓ؟�Y�a�u�����I�u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T�Ƿ������ıO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Ƿ�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�ʹ���X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Y�a�����댢���ں�̎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
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ڈ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ժ����£��炃��һλ�����ˣ��ʂ����c�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ʡ�Pһ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?sh��)؇��Y�ֵ������c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@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Y�a�r���c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ҁ�һ���̓r�I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ٸ߃r�u������ٍһ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Ū�cС�Ć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e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˰l(f��)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Ǘl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Ђ���I(y��)߀���ԏ��y��Ū����Ѻ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ǿɾʹ�l(f��)�ˡ��炃Ҳ���s�o�����Áy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^����һ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͛]ʲô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ÿ��һ���ĸ��ʩ�����߳��_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֮ǰ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҂�ȥ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L���ӣ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ȥ�@���ߵĿ��ӣ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䌦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Ј�Ҏ(gu��)�ɵ�ȫ���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Ļ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푺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ٽ����W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҂��Ľ����W�҂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˲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vijЩ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м��о�һ�£����ʹ��ЩͶ�C�߲����ڸĸ��_�ŵĻ������ߵ�̫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x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ȫ�w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ć����Y�a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�ͷ��ɵ�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�ĸ��ʩ���_һ�Εr�g��һ�δδ��r�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ٴ������ˌ��҂���ǰ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
һЩ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˻�ʂ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Փ�@����ə��Ƿ�H�H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˽�և����Y�a����Ҫָ��Щ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Y�a�����^ƽ�������ɷ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Ј��ăr��ُ�I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ɷ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҇��L�ڌ���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ĽY���ǣ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Y�a���l�ڛ]������Ӌ���ԃ�(y��u)�ݺ��a�N�ėl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ܴ_�J�l�����ٷ����Ѓ�(y��u)�șࡣ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ˎ�ʮ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ڹ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ˎ�ʮ����ϸ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ڲ�ͬ�ć��в��T�M�M���Ąڄ��ߣ��H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ƫƫ��һ�����܌��йɷ��Ƶč�λ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͟o����ȫ���ڎ�ʮ���й�ͬ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a�Ы@��һС�ݣ��@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ν�Q�@һ���}���Ƿ�Ʌ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Ӗ���
�oՓ�ǰl(f��)�_���ҡ��|�W�Ͱl(f��)չ�Ї����е��D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M�и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ˌ��T���R�r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ί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Ӌ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C�����ڷ��κ����Ļ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С��Ƿ����Ո���H��߅�C�����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҅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Ҫ���ǣ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ϰ��ոе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ܣ�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Ͳ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H�@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ڸĸ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Ĵ��r�����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