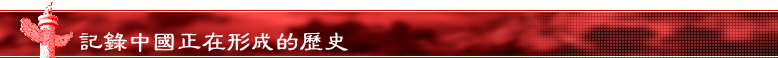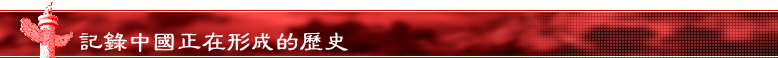|
���M
һ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(q��)֮��ȥ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`�Ѻܹ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Ȏ�ͬ�r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Ї��vʷ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c֮����Ěvʷ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`Ҳ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ޣ��ښ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Ĵ˰��ͱ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Ӱ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Ŀ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Ȥ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Đu��
�Ї��ˌ�ؚ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(z��i)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壬�Ї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(z��i)�y���ص��^ȥ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p�@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̫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n��Ԫ���@ϧ�c��(n��i)�ᡱ�������ǹŴ�Ԋ�˂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ĥ���˂���ఇ@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ӵ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r����һ��ǧ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ǧ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念�����g��һ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B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4�|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I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
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ʳһֱ��ؚ���е��˂��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Ї��˶��^�ϸ�ԣ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صĚvʷ�ރ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��x��ÿһ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ؚ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x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Ї��ˏĴ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˵��Ї��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f�r���Ľ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Bͬ�����ƶ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ʎ�ˎ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ԁ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Ї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h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^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���Ї��@��һ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ɣ�͑n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Ҫ��Q���f�f�˵Ĝ���}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ǂ��l(f��)չ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ѵ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δ��Q����}�ĵ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߅���F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
�@�ӵĵ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8Ƭ����ͬ�a������Ů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}��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̫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e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ꃱ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^(q��)����؎X���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ϵ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ص^(q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592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400�f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ر�ؚ�Fռȥ��41.5%����
ؚ�F��ζ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Ԟ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ͨ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ζ����ä�Ͱ���ä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֪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Sֻ�����뵽ؚ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ζ��ʲô��
1996�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ׄ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υ^(q��)ȥ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I(y��)ȥ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Ո��ӛ�ߺ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Щ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wζ��ؚ�����
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Ϸ�꠵�ӛ�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ˎKľ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ѷֲ����ɫ���Ʊ������e�o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һ��ȥ���ġ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gվ��ֱ�����iȦ��һ���Ϸ�D�c�iͬס��һ�𡭡�
����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ƫƧ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һ��С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ߵ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o��һλ���80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һ�ѵع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Ʊ��ӡ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ؔ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IJݷ��ӣ�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Ψ���M����ꖹ⡣����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ë��ϯ����մ�M�˻҉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Ѭ�ð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�ϯ��һĘ��\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˼�ס���@�g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ظ�ԭ�ĸߺ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ӛ��Ҋ�����ٺ���ҹ��ֱ��˯�ڽY(ji��)���ĵ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Ę�����ݡ��v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y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IJذ����Z��ƽ�o����ͬ�ڔ����e�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Ǟ��˽o���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Ҫ�s��ţ���ڱ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
�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^(q��)��ӛ��߀ �f���@��һ�����£�һλʧ�W(xu��)��С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Г쵽�ɷ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ܻ،W(xu��)У���ҵ��ώ������ώ��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˱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Ę�Ȥ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ɞ�ʹ�����ĥ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ؚ���p����߀���H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Ĵ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M��50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μ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B(y��ng)��һ�^�i�����ڵ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1�r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F����n��ס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9�q�ă���Ҳ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ֺ��e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ͬ�Ĵ��L�@�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Ә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Ǯ����L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r��ˤ�ӹ�܊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g��һ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ǜ����Ŀ��ʹ����ı��飬�l������30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ˤ�z��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е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߀�иF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οh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ӛ��Ҋ��һλ���Ўr�|��ħ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џ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S��Ę�ϛ]��һ�z���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ʴ_Щ�����Ҳֻӛ����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ħ���Dz���r����կ�ľ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|���˰�݅��ħ�ͣ����H���ܞ��l(xi��ng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��i)ȥ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B�Լ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ˡ�
ؚ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壬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Ʉӓ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y�͐u������
߀�б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Ė|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1996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겻���Ĵ�ѩ��(z��i)���R�ຣ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s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֮̎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Lѩã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C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0���z�϶ȵ�ѩҰ�������(z��i)��?n��i)��Zʳ��ȱ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ʳ��ţ�⡣�ܶ������Lѩ��ʧۙ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f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
��ɲ��ҵģ���ѩ��(z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ă��օs��ؚ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݈������^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Y����ͨ��·����ŕ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ѩ��ʧۙ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܃������ļZʳ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(z��i)����r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߀�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߀�^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ٴ�ČW(xu��)�g��ͯ��W(xu��)�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t(y��)��ˎ�������ЋD�y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ʸ��_30�����냺�ɻ���ֻ��60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@�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Ќ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Մ�l(f��)չ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ж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֮Դ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ؚ֪�����J�R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c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Q��(zh��n)
1973�꣬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韄e�Ѿõ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Ȼ��ؚ�����f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@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@ô���y����Ҍ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ڈ��ĸɲ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^���˺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ٻ����ゃ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o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ٻص����o�ޠ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y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λ���͇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ٲ����Ŀ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͇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wҲ���P(gu��n)�е�Ŀ��Ͷ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
1996��9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Lؚ����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
�ڮ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P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ɽ·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ٔ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ɽ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y���L���é�ݷ����ȱ���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ӵĴ��ͱ���Ҳ�]�Е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鮐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،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@Щ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е؆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sh��)ظɲ��f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ĸ����ɲ�Ҫ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壬�����ٔ�(sh��)�O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ʩ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Ĝ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f���ܡ��F����ɽ�o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h�͇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ˌ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ؚ�����}�ĘO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Թ��ԁ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H��ؚ���˿ڵ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ʳ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Ҫ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֮Ҫ���ڝ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Ӗ(x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ĵ�����
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ڬF(xi��n)���Ј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ӵ�Ч��ԭ�t��Ҫ���Ј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ԭ�t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؟֮һ�����ڴ��M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ȫ��l(f��)չ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ؿsС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˿�Óؚ�¸������
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ҡ���ͬ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ı��|(zh��)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x��؟�Ρ����ؚ���^�ڇ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^�ڑ��⣬�@�Ͳ������ǹ�ƽ�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H�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ͬ�r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Ά��}��
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҂���ҕؚ����࣬��ʩ��ؚ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Ҫ����ؚ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Ї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h�˳��f��һ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Ҳ�nj��롶���Ұ��߷�ؚ����Ӌ�����ĵ�һ��Ԓ����
��ؚ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ƽͬ־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ѳɞ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1994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҇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ˡ����Ұ��߷�ؚ����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Ҫ����7�����ҵĕr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r(n��ng)��8000�fؚ���˿ڵĜ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ľV�I(l��ng)��Ӌ�������
1995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籾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χ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h�ϣ��ٴΏ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ĈԶ��Q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ؚ����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
1996��9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_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ٴ����_��Ŀ�ˣ��ڌ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ؚ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ȫ��6500�fؚ���˿���K��Q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˿��ӆT��ӿ��ؚ�_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@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ġ����o֮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
40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h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Ї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չ�_��һ��܊�´�Q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µ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H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Ҳչ�_��һ����Q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ص�˦����ؚñ�ӣ����F(xi��n)ȫ����Ĺ�ͬ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Ҳ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^��ؚ����ò�č����ˑB(t��i)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Q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40����ǰ���Lj���Q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D�y�͉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ˎײ�
50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f���ġ�(li��n)�χ����¡���50���^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ؚ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(li��n)�χ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ߵĴ�������@ʾ犡�ָ�ÿ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ϱ�a(ch��n)��47��ؚ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s��6.7�f�ˡ�
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ڡ�1990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桷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80����ǸF�˱��z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ȥ��1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罛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ؔ��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}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_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я�27�����ӵ�48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˿ڽ������10�|���ӵ�13�|�����Ŀǰ߀����ÿ��2500�f�˵��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l(f��)չ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н�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̎�ڳ�ؚ֮�У�ÿ����1000�f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͠I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Ќ�����21���o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c���γ��r�����յ��ǣ��ĸ��_���ԁ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^��ؚ���˿ڏ�1978���2.5�|�p�ٵ�1996���5800�f�ˣ�ؚ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ʏ�30.7%�½���7.1%����Ї�ؚ���˿�ռ����ؚ���˿ڵı������я�70���ĩ���ķ�֮һ�p�ٵ�Ŀǰ�Ķ�ʮ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u֮�顰�Ї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
ȡ���@�ӵij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ڸĸ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ķ�ؚ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҂������c�䌍�ܵͣ�1978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7.9�|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볬�^300Ԫ�ăH��0.1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84%���˿ڣ�Ҳ����6.6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200Ԫ���@��һ�l���H���J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һ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У���δ�_ʼ����
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x�͵ľ��ǃɼ��£���һ�Ǹĸ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Ó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f��80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幤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Óؚ����
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¿ɷ֞������A�Σ���һ�A���Ǐ�1978�굽1985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ؚ���˿ڴ���Ȝp�ٵ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ĸ�l(f��)�ˏV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e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ߣ�ȫ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δ��Q���ؚ���˿ڏ�2.5�|�p�ٵ�1.25�|������
1988�꣬�����y�аl(f��)����һ�݈�棺���Ї���ؚ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c�����y�еIJ��ԡ�����挦�Ї��ķ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1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Ĝp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w�Ƶĸ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ɴ˼��l(f��)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sС��ؚ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Ƿ�ؚ�ġ��ĸ(y��u)�ȑ�(zh��n)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(j��)�ǣ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ȷ��档�f�w�Ʋ��H�S����ؚ���˿ڵ����е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Ƽs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ֻ���ڸĸ��f�w�ƵĻ��A(ch��)�ϰl(f��)չ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Ч�ؽ�Qؚ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w�ơ�
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ʩ�ĸĸ(y��u)�ȑ�(zh��n)�ԣ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ጷ����Ʉڄ�������^ȥ�Ї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ôؚ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Ƿ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˂�֧���Լ��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dz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ؚ���@���~�Լ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_չ�нM������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ģ�ķ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ڵķ�ؚ�����Ǿȝ��͵ģ����Ќ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8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)Ժ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¡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M�����c��ؚ���O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2�|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S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ڶ��A���Ǐ�1986�굽1993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ؚ���˿ڷ�(w��n)���p�ٵ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ؚ���˿ڏ�1.25�|�p�ٵ�8000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1986�꣬����(w��)Ժ������ؚ�_�l(f��)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С�M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Ҫ�Ćμ��ȝ�����ȝ��_�l(f��)���D(zhu��n)׃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҇��_չ��ؚ�ԁ�����̵��D(zhu��n)׃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Փ�������نT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ߣ�߀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J�R�����ľȝ����_�l(f��)��׃ݔѪ����Ѫ������Óؚ�¸��ı���֮·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A�Ώ�1993����_ʼ���@�Ƿ�ؚ���D�y�Ĺ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ˌ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o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ؚ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롢����(w��)Ժ���_��һϵ�о��w�����^Ӳ�Ĵ�ʩ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ƶ��͌�ʩ���Լ��ķ�ؚ����Ӌ�����Ĵ��Ąڄ�(w��)ݔ�����½��ġ��ڰס���(zh��n)�ԣ�ʯ�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ġ����S��ؚ��ȹ��̡����V���Į����_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@��ζ����ؚ�_�l(f��)�Ĺ��R�ѽ�(j��ng)�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ڊ^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Óؚ���ԡ�
�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ƶȷ�ؚ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̡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@һϵ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IJ�ͬ�ӴΡ���ͬ��(c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չʾ��ȫ����鷴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ۺ�Ŭ������
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oĩֻʣ��3��ĕr�g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ϵĴ�Q��(zh��n)�ѽ�(j��ng)�M�뵽�˹����A�Σ�
���ģ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̎
��ؚ���ԣ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
ϣ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ࣺܶ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)Ժ�ĸ߶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_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ɲ�Ⱥ���[Óؚ���ď���Ը���ͷe�O�ԣ����ض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ͷe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֮��Ч�ijɹ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10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Ļ��A(ch��)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Ұ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İl(f��)չ�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����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ѵõ�ȫ������Jͬ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C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F�w����Ĵ��г��е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l(f��)�_�^(q��)��Ͷ�뵽��ؚ�I(y��)�е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Խ��Խ���@��
�y�ȴ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҇�ʣ�µ�ؚ���˿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30Ԫ����Ľ^��ؚ���˿ڡ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з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^(q��)��ʯ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Į�^(q��)���ߺ�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߅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ƫ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㣬�Y���T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y���Ƿ�ؚ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е�Ӳ���^��
�҂����͇����u��İ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K�Aб���İ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ɸ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d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؉��ϸ�ԭ����(j��ng)̫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ֱ����X��һ�l����Ԓ���@�l�����ԷQ֮��ؚ���ֽ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ؚ���˿ڽ^�ֲַ����@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(j��)�y(t��ng)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ؚ���˿�ռȫ��ؚ���˿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92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hռؚ���h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50%�����ɽ�^(q��)ؚ���h��378����ռؚ���h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64.4%�������ٔ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ؚ���h��258����ռؚ���h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43.6%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ҽy(t��ng)Ӌ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Y�ϣ���1993���1994������gÓؚ��1000�fؚ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в��^(q��)��ռ��80%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ֻռ20%���Q��Ԓ�f���ȫ��ÿ��p�ٵ�500�fؚ���˿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100�f���
�F(xi��n)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ĩ�������ֻʣ�������ĕr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ÿ����Ҫʹ1500�f���ϵ�ؚ���˿ڽ�Q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@�ஔ���^ȥ�ٶȵ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000�f���ҵ�ؚ���˿ڵĜ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o��
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߀��Ҫ��ؚ����Փ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2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ĸ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ǧ�fؚ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Óؚ�¸��ĵ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Ј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Mһ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Ȼ�Ľ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L�^�̴���Ȝp��ؚ���˿ڵĺ��C�A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֮���ǸF�˾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ְl(f��)չ�A�Ρ�
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Ј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l(f��)չ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l(f��)չ�̶ȵą^(q��)����̎�ĵ�λ�Dz�ͬ�ģ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c�IJ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ӄݵĵ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øF�˵����汻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ԣ����Ј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ؓЧ��(y��ng)ռ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λ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˿ڲ������ܔ[Ó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Ј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֮�⣬����ؚ���Đ���ѭ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һλ�L����ӡ�ȏ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}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Ј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ױ���ҕ��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ؚ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_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ؚ���˿ڿ���(sh��)�½���ռԓ����?c��)˿ڵ?0%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@Щؚ���˿��y���ڶ��ڃ�(n��i)ͨ�^ȫ��Ľ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L�[Óؚ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
�߳��@�ӵĐ���ѭ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һ�㽛(j��ng)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ķ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ؚ����Փ�͌��`��ȫ�愓(chu��ng)�¡�
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ڞ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ؚ���˿ڶU���ߑ]��ͬ�r���߀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ӛ��һȺؚ���˿ڵĴ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Ⱥ���
�M��90����ԁ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н�(j��ng)���w�Ƶ��D(zhu��n)܉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ͣ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a(ch��n)��̝�p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ˆT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еğo�I(y��)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�ؚ���˿ڵ����С�Ŀǰ�����@�ӵ�ؚ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ǧ�f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ؚ���c�r(n��ng)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�ؚ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ܳ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Óؚ���k��Ҳ���M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Óؚ�o��Ҳ��(y��ng)ԓ�ɞ鷴ؚ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۵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
5800�fؚ���˿ڡ����@һ�|Ŀ�@�ĵĴ��ژ�(g��u)���˱����oĩ�Ї���һ���y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@���y�}���t�ɾͿ����oһ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y�}�����t�o���˺���һ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һ�P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
��ؚ�����e�o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Ҵ���
�@�ǚvʷ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
��Сƽ��ؚ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Ҫ���O(sh��)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Ѓ�(y��u)Խ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[Óؚ�F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ĩ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Q��8000�f�˵Ĝ���}���ռ�����˿��ķ�֮һ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˙�(qu��n)���}���Ĵ˾͏ص�Q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H���҂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Ěvʷ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չʷ��Ҳ��һ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
���i��ȫ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w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h�Ļ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@��Ҫ���أ��@��Ҫ��ؚ���^(q��)�Č��H��r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ѷ�ؚ�_�l(f��)���齛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QȺ���Ĝ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΄�(w��)��
1978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ؚ���˿ڞ�2.5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
1985������p�ٞ�1.25�|��
199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ٜp�ٞ�8000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1995�������ٜp�ٞ�6500�f������
1996�������ٜp�ٞ�5800�f�ˡ�
Ŀǰ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ؚ���˿�ռ����ؚ���˿ڵı������я�70���ĩ���ķ�֮һ�p�ٵ���ʮ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ʏ�1978���30.7%�½���7.l%������
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Ŀ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Ȥ��
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y�͐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֮Դ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ؚ����ȫ��Ĺ�ͬ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
(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1997��5��20�ա������Ոڶ��棩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