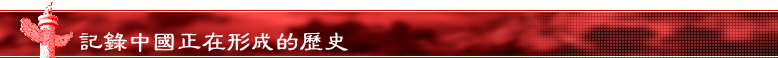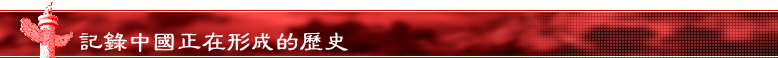|
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݆�Q��
���M(j��n)
һ��ǰ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ھ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ú�ˮ���rѪ�Qȡԭú�IJɾ�9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Vɽ�˸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ɸɾ͘I(y��)�T·�ĔU(k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V�й�Խ��Խ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Ը�x��ú̿�И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ڔ[Óؚ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ȡ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b��)�˾��ڄ�(d��ng)���ľ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y(t��ng)Ӌ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1992��5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(gu��)22��(g��)ʡ�������241��(g��)�h�й���8212λ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˾����˴�ú�V�ĵ،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˵V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ھ��µ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ĵ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V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ú�m�ڟ�Ѭ����ڵ�Ę�������ǘO��ƣ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Fһ�ӵČ�?k��)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V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V�f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u�ij��Ű�Ȼ����·��@����ǹ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
�Ұٸ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挦(du��)�@Щ���ܰ��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B(y��ng)���^�҂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ֵ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ĸF�l(xi��ng)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c��)ڹ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ײ�͛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c��)ڸ�׃�Vɽ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̵ظ�׃�Լ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ͬ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݆�Q������
�R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@һ˲�g������t�е���ǰ��δ�е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һ��(g��)ֱͦ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
1989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2000��Ԫ��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ľ�ǝ�ú�V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H21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7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Ǻӱ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ͯ�겻������8�q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H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Ơ����ļҺ�1000��Ԫ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ډ�(m��ng)�У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W(xu��)һ�꼉(j��)���z�W(xu��)�ؼң������_Ѿ��ɽ�ټ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ɲ�ˎ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N�a(b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dz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14�q�r(sh��)�x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f���˷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ǃ��x��ֻ��3��5����أ�һ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»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ۺ�؟(z��)�R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�����Ϣ�ĺӰ����ͼ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һ��֮���ܵø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^�ϣ��ڜ��ݟ��^�u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ƽ��܇��1989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˾ˎ�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ľ�ǝ��V���@�Ž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ú�V�Ļ(du��)���㲻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oՓ�DZ���2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200����б�£�߀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Ļ����ǰ���ܵĿ����Ҳ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Ԓ��ֻ��һζ�����^�ɻ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ϵ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199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韄e7��֮�õĹ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g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ڼ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߀�XҲ�]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ܴ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ģ���Ҫ��(zh��ng)�⣬߀���@�P�X������
�ص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Ъ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X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Щ�X������ͼĻؼ�߀�����
1991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λ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̧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ϸ��H�ӵ��V�Ͼ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ͦ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ס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lҪ�Xȥ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�f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f(xi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Խ��߸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6����ǰ߀�����Ђ�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Ͳ�픂���
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s�ϰ����r�t��ָӡ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r�t��ָ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`̤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ɂ�(g��)�º�����t�ط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ɽ������з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т�����Ո(q��ng)���T��ž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œ������ϣ�
����Ҳ��֪��Ƿ�˶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ゃ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ΨΨ�Z�Z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ӿ�����^��18��Ă�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P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P�P�壬��ͬ�����Ŀڵāy��һ�z�z��ȥ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ĵ�һ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ͦ�ظ�e�˹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ǰ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@һ˲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е���ǰ��δ�е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ֱͦ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Ρ�
���Z¡¡������˯�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|��߀�� ���R�_(d��)�Z�Q�����30����ص��L(f��ng)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ﲻס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ǧ��֮�b������ǃ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ص�Ⱥ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͉�(m��ng)�ßo��ظ��_�ˡ����Ю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|���ڼҷN��6��ء��Տ�(f��)һ��ɢ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ڄ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M�㲻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ڴ���đ��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݅݅�ľ۾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ȥ�J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ۻ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V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(y��n)��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��ۉm�ܵ���ɤ���ۡ��첲�������첻�_�����С�ľͿ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@����ꖹ����敳�������൹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һ���ú�V��ȫ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X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۵�߀�Ǹɻ�������ڎr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챧���L(f��ng)�N��rʯ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o����Ӗ(x��n)Ԓ�f�����Ђ�(g��)݆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V�����ˣ�߀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ng)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g)��ֻ����һ�룡���ܴ˽�Ӗ(x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ϰ�ͱ��o�L(f��ng)�N�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첲�۵�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ĸ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ʈ@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˵�Ӱ������Ҍ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(m��ng)�С�
�����x�қ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q�ĺ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ܵ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Q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ӛ]֪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]���µ��ˣ����ă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𣬾ͺܝ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M����ˣ���߀��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;���(j��ng)�^����(g��)�µ�ϴ�Y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˱���ʽƸ�õ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׃�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
һ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ɴ��M(j��n)�ǻһ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x�_�Vɽ���
1989��12�µ�һ�죬���f���°�����ڵV�^(q��)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ͻȻ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͆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±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Ȣϱ�D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±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ӡ�һ �@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û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һ�ж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±����z�w�ѽ�(j��ng)̧���ρ���
˷�L(f��ng)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ĹǻҺ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ںӱ�ʡ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С�G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қ]�Ў��ú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ә�p�I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f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y�^��һ��ǰ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Ҳ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Ĺǻһ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ȥú�V�ģ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Ĺ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ô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f��ԭ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صص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ܰ����ڮ�(d��ng)?sh��)ؔ(c��i)?sh��)һ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35�q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x�_�^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8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ǝ�ú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̱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V�ϡ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f�ɻ�ɻ�f�°���°�����°���Կ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ʲô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һĘ�Ŀ옷�͝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ص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fú�V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ׂ�(g��)�˸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ڶεăɂ�(g��)�˸�(j��ng)���^���y����
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ͬһ��(g��)ú�V���˃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ǿ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ص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Ȼ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Q��Ó�˼��˵���r���ص�ԭ���č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ӣ�ƽ�o�ڄ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ܵĺ��f����
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ɞ�һ����ʽú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L(zh��ng)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ɂ�(g��)Ů����߀Ҫ��Ū��؟(z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ص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̲�ͣ�ظɻ������ƺ�Ҫ���a(b��)��(du��)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dz��ې����ăɂ�(g��)Ů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Ů���ӵ��V�ρ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Ů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ܺ��ߣ����ٵ�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鸸�H�����ĝ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Є�(d��ng)ʎ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r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(d��ng)һ��(g��)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Ю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һ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Ȼ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^ʹ��һ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ʼ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ð�U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֣�һȥ1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J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l(f��)��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עһ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ɹ��^�� 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ӡ��ֻ��һ�B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1988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ӌ�(sh��)�ڸF�Û]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ĸ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]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u�����мҮ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yȫ���x�_�˹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
�R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ٸ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ܾò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ˡ���ע��Ҫ���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R(sh��)�օs�dz������t�ݵ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ﰵ�Q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Ҳ���e̎ȥҪ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?c��)���ƽ��V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V��߀�Džf(xi��)�h�(du��)�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ð���L(f��ng)�U(xi��n)���J��а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r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Ё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]�՛]ҹ�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ٻ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˯�X�Еr(sh��)���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V�¶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M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¹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N�s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΄�(w��)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̝��1�f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ٴ�׃�u�Үa(ch��n)���o���˰l(f��)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m(x��)��ɣ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Ť̝��ӯ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)�h�(du��)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®�(d��ng)���(du��)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[�X��ƣ�롣���͵V�Ϻ��ĺ�ͬ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Ǖr(sh��)��ȥ�Ώ����һ���˵���Ӌ(j��)��ΰ��ţ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37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y�����Ψһδ׃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ֻ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һ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x�_�˵V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f���@���£���ƽ��V��ú���ι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ϯ�����Ͼͺ�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Ԓ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(hu��)�¾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T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8�q����ú�V݆�Q������?xi��ng)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ͬ�ڝ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푪(y��ng)�o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ӣ��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V���V�ϵěQ����ֻ�f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ȥ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T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Ҫ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]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T��(gu��)�겻�ɣ����ڵV���@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ā�]Ҫ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ߺߵ��¾��ˡ�
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࣬һ�Kʯ�^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
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(gu��)�ꮔ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Ѳµ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һ�П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еķ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�꺹ˮ�ĵVɽ��e�����
�R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т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x�_�˵Vɽ���
���յ��x���ѳ��^ȥ���͢���oȥ�˸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ȥ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
�͢�������ֺ�һϵ�кպՑ�(zh��n)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8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x�]������ɽ�V�����3��(g��)�º�ͮ�(d��ng)�ϰ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1988��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С���ɂ�(g��)���ѣ���֧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9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a(ch��n)Ӌ(j��)��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88��1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�����V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10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˳��a(ch��n)33���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(g��)�˪�(ji��ng)����_(d��)500Ԫ��
1990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˱����С���һ�ڄ�(d��ng)��(ji��ng)?w��)¡����͢������Ξ?�θ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ȫ�ι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ҹֻ˯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С�r(sh��)��ǰ�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¾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Σ�U(xi��n)�ض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픍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9�c(di��n)һֱ�?sh��)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?2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䡱�ĽY(ji��)���s�ǣ�6��4��(g��)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΄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Ҳδ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�£�ƣ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͢���K���Q���oȥ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³ɞ�һ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ܲ��L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Ǹ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]�еõ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̶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]�W(xu��)�^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ټ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݆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Dz���ָ�]һ��(g��)�Σ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
���o����݆�Q���еă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܌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ij�Խ�����յ��x���ѳ��^ȥ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ˮ�X�ϡ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Ҳ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˰��ĺ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5������ţʢ�@����ʯ���f���ĺ��ڌW(xu��)Ժ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I(y��)�ĽY(ji��)�I(y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d�^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ɸ����ص�ʧ��s�u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خ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ˡ��ڷ��صĄڄ�(d��ng)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gһ��(g��)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挦(du��)�Ұ��ĉ��ڣ��D�y���½�(j��ng)�^���`���^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һ�ζΌ��o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Լ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ЌW(xu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ͺ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ù�Ԋ������һ�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Ć��ɽ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89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V����@ϲ�ذ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ЈD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Ąڄ�(d��ng)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߀�ǽ�(j��ng)���o�˵ؑ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࣬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���һ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ָ���ĆΓ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ͱ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ʹ���p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ڌW(xu��)Ժ���ώ����ŃA�V���е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̫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ʲôҲ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ŗ��ˡ�����
�ܿ죬�ώ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ώ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Ҫ�ɳɹ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͕�(hu��)�ص��ˡ�����
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X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⽹�꣬�·���ص�ɫ�ʶ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ϼң��ӱ���ǿh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ǃ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տ�{(l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՚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d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ĸ�����ό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ĸ��H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H���_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ᅡ����ʰ�øɸ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@һ�Еr(sh��)��Ŀ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ؚw�ʈ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S�����DZ˰��ĺ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վo���еĹ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݆�Q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۳��@��һ��Ԋ��
���_�ˣ��^�?sh��)V���Ĵ��T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ϣ��泯�S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cԭú���ߣ��nƱ�c��ԣ�Y(ji��)�]������˼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飯��ߴ٣���ҹ���Ǒ���
�Ǽ��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܉�ǃɸ����}��Ѫ���|ײ�������܇��ѪҺ����
β
�҂�ÿ��(g��)�˶���(du��)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݆�Q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IJ�ͬ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֞����N��ͣ�
���ڸ��t�@�ӵ��ˌ��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ɽ������Ǟ��˔[Óؚ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ĸ�ʹ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e����݅��ήή�s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ؔ(c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ͦ�����U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ڵ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ƳҊ�˺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ʽ��(g��u)�ɵĠI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Z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ʹҪ�������r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Ը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Ӱ�҂�����Ϥ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پ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Ҳ�S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`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o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ţʢ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ij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_ͣס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Ҳ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(hu��)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߀Ҫ�ߺ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ܺܶ�ܶ�����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(hu��)�и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l�o�M��߅��֮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_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A �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R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ϡ���Էֱ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|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1992��10��2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?q��ng)?b��o)�����İ棩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