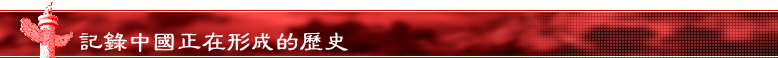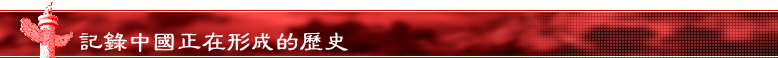|
熊 蕾
是搖籃也是殺手,是母親也是威脅����。自古以來��,中國對它的大江大河就是既依賴��,又擔(dān)心��。黃河就是其中的典型��。
清朝時期����,黃河的治理已經(jīng)被認(rèn)為關(guān)乎王朝的穩(wěn)定,乃至朝廷專設(shè)了一個級別上僅次于宰相品位的專門負(fù)責(zé)黃河事務(wù)的河道總督衙門�����,特許河道總督進(jìn)紫禁城不下馬�����。但是一旦洪水決堤���,則要人頭落地��。
1998年夏天���,當(dāng)人們關(guān)注著長江和東北的滔滔洪水時��,這條中國的第二大河面臨的困擾卻完全不同:黃河再次因缺水而斷流。自1949年以來���,為了防洪�����、發(fā)電等目的��,在5465公里長的黃河沿線已建成8座大壩���,還有4座正在建設(shè)中。它們和下游黃河中的涓涓細(xì)流���,形成了鮮明的對照�����。
"最使我震驚的是��,1997年7月到9月90天的洪水期�,黃河利津站──黃河入海前最后一座水文站──竟斷流72天!"黃河水利委員會副主任�����、總工程師陳效國說��。
1997年全年����,位于山東的利津站記錄的黃河斷流天數(shù)總共達(dá)226天。這是有史以來最嚴(yán)重的斷流��。1998年截至7月31日��,該站的斷流記錄是118天�。根據(jù)黃委會的研究,黃河每年入海水量應(yīng)為200億立方米��。但1997年實際入海的水量僅為18億立方米��。
"中國的憂患"
由于造成的災(zāi)難不斷��,特別是在人口稠密的中下游地區(qū)造成災(zāi)害,黃河歷來以"中國的憂患"而聞名����。從1962年起同黃河打了近40年交道的陳效國說,黃河曾讓他和同事們一年到頭擔(dān)驚受怕:"夏���、秋季當(dāng)然要防洪����,而冬春之交的凌汛也不得了��。"
從公元前602年的周定王5年到1938年的2500年間��,黃河決口不下1590次�����。僅1896年到1946年的50年中����,黃河就決口210次���。同時����,由于黃河流域復(fù)雜的地質(zhì)構(gòu)造和地質(zhì)運(yùn)動,黃河下游一次又一次改道��。所以�����,陳形容過去的黃河是"三年兩決口���,百年一改道"�。每一次決口和改道�,都是一場災(zāi)難。而黃河的水患�,罪魁禍?zhǔn)资悄嗌场|S河中游經(jīng)過的大部分地區(qū)�����,是風(fēng)化侵蝕嚴(yán)重的黃土高原����。東漢張戌就曾指出:"河水重濁,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�����。"意思是說,沙比水多�。汛期泥沙量則更大。進(jìn)入下游����,水流減緩,大量泥沙便淤積在河道中����,使河床抬高。據(jù)陳效國說��,多年來���,下游河床平均每年抬高5至10厘米。目前下游700公里河道平均高出地面3到5米���,有些地段竟高出地面10米以上����。黃河由此成為"懸河"�����。
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鄂競平說,歷史上的河道總督����,職位高責(zé)任也大。黃河如決口��,不僅現(xiàn)任總督要遭凌遲處死����,滿門抄斬,而且他的上兩任總督也要被砍頭��。"因此�����,"他說�����,"清朝的河道總督有不少在決堤時����,跳水自盡����,以保全家人����。"
如今,這種殘酷的刑罰早已取消����,但治黃的人們依然感受著一種沉甸甸的壓力。用黃委會山東河務(wù)局總工程師張明德的話說����,就是"如臨深淵,如履薄冰"��。他從1961年起干河務(wù)��,多少年��,春節(jié)不能和家人團(tuán)聚���,怕的是黃河凌汛;一入夏又晝夜值班防洪,"真的是提心吊膽"�����。
過去"三年兩決口"的黃河�,已經(jīng)50年沒決一次口了。陳效國說��,這是"人民治黃的偉大成就"�����。僅此一項����,就等于為國家創(chuàng)造了4000億元的效益。他說����,上中游建的大壩"有效地增強(qiáng)了我們抗洪防凌的能力"。但是今天面臨的卻是新的問題:黃河來水不足乃至斷流的問題����。
斷流
自1972年以來的26年中,有21年發(fā)生了黃河斷流�。自1991年以來���,年年都發(fā)生斷流。而且��,張明德說��,斷流的天數(shù)不斷增加��,斷流的河段也不斷延長�����。1997年��,斷流河段長達(dá)700公里����。但是,斷流決不意味著防洪任務(wù)的減輕��。相反���,張明德說�,斷流更加劇了洪災(zāi)的威脅��。因為黃河洪災(zāi)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泥沙淤積�����。
正常情況下�����,黃河來水每年應(yīng)將10億噸泥沙沖入渤海�����。但是現(xiàn)在水量減少��,每年入海泥沙量只有2億噸�����。"這意味著大部分泥沙都留在了主河道里��。一旦洪水來臨���,水道堵塞��,就會發(fā)生漫灘����,出現(xiàn)險情,"張說���。
1996年8月���,下游地區(qū)就出現(xiàn)過這種"小水大險情"。當(dāng)時洪峰流量不過每秒4000多立方米�����,卻造成了通常每秒一萬立方米的高水位���,幾乎超過下游堤防最大的防洪能力����。"而且洪水通過時間也延長了──過去洪峰從兩個水文站之間通過只需幾個小時���,現(xiàn)在則可長達(dá)幾天�����,"他說�����。"所以�,斷流使防洪形勢更加嚴(yán)峻����。"
"厄爾尼諾"
一些科學(xué)家認(rèn)為,黃河斷流的部分原因��,在于不利的自然條件���。中國科學(xué)院院士�����、地理學(xué)家吳傳鈞說��,黃河是"先天不足"�。
首先����,黃河流經(jīng)的地區(qū)大部分是干旱半干旱地區(qū),年降雨量只有200到500毫米����。"所以黃河不是一條水量豐富的河流��,"他說�。號稱中國第二大河����,黃河的徑流量只排在第四位,最大流量一年不過580億立方米���,而長江則是一萬億立方米��。
其次�����,吳說�����,黃河形成的歷史很復(fù)雜���,流向"很不自然",其中包括很多90度的大拐彎,而它流經(jīng)的很多地理帶�����,如青藏高原��、黃土高原�,"個性都比較強(qiáng)"。特別是黃河河段最多集中在黃土高原����,而黃土高原的堆積很松散����,一下雨就沖刷,使黃河成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�。
中科院院士、大氣物理學(xué)家陶詩言說��,氣象因素使問題更加復(fù)雜化�。他說,中國北方6個氣象站的氣象資料表明��,自1965年以來��,黃河流域的年降雨量比正常水平減少了20-25%�����。特別是1997年,斷流河段長達(dá)700公里��,更是異常��。其部分原因就是厄爾尼諾現(xiàn)象加劇了已經(jīng)比較嚴(yán)重的干旱�。
然而,陶指出�,1997年的干旱并不是歷史上最嚴(yán)重的。在1920至1940年的干旱周期�����,黃河流域年降雨量曾銳減過35%����,最旱的一年黃河全年總徑流量只有220億立方米。而1997年的總徑流量是250億立方米��。但在1920-1940年周期����,黃河沒有出現(xiàn)過斷流。因此,陶說����,水資源先天不足和不利的天氣條件,"不完全是"黃河斷流的決定性因素���。
用水過量
陶��、吳等科學(xué)家今年7月沿黃河進(jìn)行了15天的考察后認(rèn)為�����,黃河斷流的主要原因在于,"對黃河水的過量使用超過了黃河的承載能力"�����。
水利部水利科學(xué)研究院水資源研究所總工程師王浩說���,黃河盡管為患不少��,但自古以來卻以其有限的水資源哺育了近半個中國�����,而且是中華文明的發(fā)源地之一�����。他說����,"中國以農(nóng)業(yè)立國,農(nóng)業(yè)又是灌溉農(nóng)業(yè)��。90%的經(jīng)濟(jì)作物和70%的糧食作物依靠灌溉�。"而中國的水資源分配卻很不均衡:長江以北的農(nóng)田面積占全國農(nóng)田總面積的60%,但水資源只占全國總量的18%����。
黃河流域的問題,可以說是中國面臨的水資源窘境的一個縮影����。王浩說,1995年的一個調(diào)查表明�����,中國的水資源總量在全世界153個國家和地區(qū)中排在第122位��,人均每年只有2300立方米,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���。而黃河流域的人均水資源擁有量���,僅為全國水平的四分之一。
在黃河流經(jīng)的寧夏回族自治區(qū)��,年均降雨量只有305毫米����,而年均水蒸發(fā)量卻高達(dá)2000毫米。寧夏人靠黃河灌溉的歷史已有兩千多年���。所以�,寧夏自治區(qū)委書記毛如柏說�,"沒有黃河就沒有寧夏�����。"
黃河幾乎是擁有528萬人口的寧夏唯一的一條大河�,占寧夏灌溉用水的80%。據(jù)自治區(qū)水利廳統(tǒng)計�����,至1997年底,寧夏的農(nóng)田灌溉面積已從50年代初期的31萬公頃擴(kuò)大到41.2萬公頃�����,糧食產(chǎn)量則從16萬噸增長到250萬噸��。
據(jù)陳效國說����,黃河流經(jīng)的九個省區(qū),引黃灌溉的農(nóng)田總面積已達(dá)500萬公頃�����,而50年代初只有140萬公頃�����。農(nóng)業(yè)�、工業(yè)和城市生活引用黃河水的用水總量則從50年代初的每年122億立方米增長到90年代的300多億立方米。"一般來說��,一條河的水資源利用率達(dá)30%就相當(dāng)高了��,"他說。"黃河的水資源利用率已超過50%�。"
浪費(fèi)與潛力
中科院院士、水資源專家劉昌明說����,在每年超過300億立方米的黃河用水總量中,農(nóng)業(yè)用水占92%��。而有效灌溉系數(shù)��,也就是真正澆到地里的水量�����,僅為30%�����。水的浪費(fèi)是驚人的�。
在這巨大的浪費(fèi)中,中國農(nóng)業(yè)科學(xué)院的灌溉專家賈大林看到的是巨大的潛力�����。他舉例說�����,用同等量的黃河水�����,陜西涇惠渠灌區(qū)的灌溉面積是8萬公頃�����,河南人民勝利渠灌區(qū)的灌溉面積只有4萬公頃��。"這其間的區(qū)別就在于涇惠渠灌區(qū)采取的防滲措施���,賈說����。而涇惠渠灌區(qū)在這方面還不是做得最好的�。
目前,沿黃河已經(jīng)建起122個引水工程引黃河水供應(yīng)城市生活�����、工業(yè)和農(nóng)業(yè)灌溉用水����。但渠道防滲防漏的襯砌率只達(dá)10%�。賈大林說����,如果襯砌率能再提高10%,就會節(jié)約用水30%���。所以����,他和很多科學(xué)家認(rèn)為�,解決黃河水量不足的當(dāng)務(wù)之急是"節(jié)流"。
專家們提出的另一個建議是���,起草"黃河法"����,以加強(qiáng)對黃河水資源配置的全面管理����。中科院院士、生態(tài)學(xué)家孫鴻烈認(rèn)為,目前存在的黃河水利委員會��,只是水利部的一個下屬機(jī)構(gòu)�����,對控制調(diào)度全流域的水資源權(quán)威性不夠�。比如對黃河日益嚴(yán)重的水資源污染問題���,它就幾乎無能為力����。
目前����,在國務(wù)院主持下,對沿黃各省區(qū)每年引黃的水量����,有一個分配方案。如寧夏每年分配的引水總量是40億立方米�,山東是70億立方米。但是�����,陳效國說,黃委會既無手段又無權(quán)力來監(jiān)督這些分配方案的實際執(zhí)行情況���。至于專為一條河立一個法是否有必要����,專家們認(rèn)為:黃河的情況太特殊�����,它所起的作用和面臨的問題在全世界都是獨(dú)一無二���,因此專為黃河立法�����,并不為過�����。
與此同時����,科學(xué)家們還主張?zhí)岣唿S河水的使用費(fèi),征收水資源費(fèi)�。王浩說,黃河水之賤同黃河水之稀缺�,令人難以置信地不成比例。比如農(nóng)業(yè)灌溉用水����,使用十立方米的水費(fèi)才相當(dāng)于一瓶礦泉水錢��。
借用長江水
科學(xué)家們認(rèn)為���,從長遠(yuǎn)的觀點(diǎn)看���,解決黃河水資源不足的根本措施是"補(bǔ)源",即調(diào)長江水來補(bǔ)黃河���。
現(xiàn)已提出的調(diào)水線路有三條�����。東線是從長江下游調(diào)水���,但主要是解決華北的缺水問題,擬跨越黃河,所以同黃河直接關(guān)系不大����。中線是從長江中游的漢水附近引水。路程最短但也最棘手的是西線──在青藏高原穿山鑿洞�����,直接以長江及其上游支流源頭的水為黃河補(bǔ)源�。
王浩認(rèn)為,只有西線調(diào)水會使整個黃河流域受益�。黃委會一些工程師從一參加工作,就專門研究西線的調(diào)水線路���,有的至今已研究了40年���。而研究仍在繼續(xù)。
對整個黃河的研究��,也遠(yuǎn)未有止境����。無論陳效國、張明德這些"老黃河"�����,還是水利部年僅34歲的總工程師、被稱為"水利規(guī)劃專家"的李國英�����,都認(rèn)為�,我們對黃河的認(rèn)識,"未知數(shù)仍大于已知數(shù)"�。
李國英引用水利部前任總工的話����,說明黃河在水利工作者心中的分量:"我的精力,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是在黃河上����。而黃河的問題,占第一位的仍是防洪�。因為黃河不來水則已,一來水就非常難辦��。"
所以�����,李國英說,黃河下游700多公里長的河段���,"不僅懸出地面���,也懸在河務(wù)人的心上。"
它也懸在所有關(guān)心這條河命運(yùn)的人的心上�。
(原文是英文, 1998年8月22日載于英文《中國日報》����。中文譯文發(fā)表在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。)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