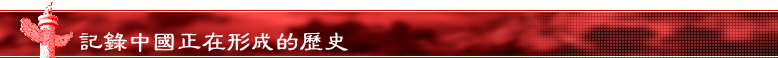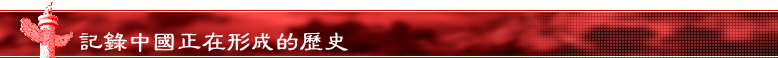|
����
83�q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p��ĺ��@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ͯ�B(y��ng)ϱ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7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70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ס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1100���Ď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Ĵ�ʡ���h�h���ɽ��̎ǰ��߅��һ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픡�
�r�����З�ҵ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ѹ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g�Ђ�(g��)���T(m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ǎr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һƬ�������Ҋ(ji��n)�ס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(ji��n)ª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˺���̫�ɂ�(g��)С�OŮ��"�P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߅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ľ�崲����
"�҄���(l��i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é���ݣ�"����̫�ؑ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X(q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ֵĺ���̫�f(shu��)���ϼ��ﱳ�˶��ق�����ֻӛ��ֱ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60�����ȥ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P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һ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и����w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ȏĺ����w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c��)�ƽ�΅^(q��)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��)�s��Խ��(l��i)Խ��Ĵ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̫���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ּܷ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麞�鵽ס���@�r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ϼ���ǰ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͵�ɽ�����_(k��i)�ĵ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ס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ñȗ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h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Ȫ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´壬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ʮ���˼Ҷ���ǰ���ɰ��Ĵ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ͺ���̫һ��ס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�Ӄ�ϱ���O���Oϱ�����̓ɂ�(g��)ʮ��(l��i)�q��С�O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OŮ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7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ϷN��8���ء���ɺÕ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t����߀��ЩС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˞�(z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50�q�ă��ӗ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"�Ǿ�ʲô�ճ�Ҳ�](m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1991�����һ��(ch��ng)ɽ����f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ȝ�(j��)�ͽ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(l��i)�ģ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ʹ��"���꾰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ճ�Ҳֻ��ȫ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"�҂��](m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10�^�i��12ֻ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һЩ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ϼZ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i"�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90����y�u(m��i)���Ãr(ji��)�X(qi��n)"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i��Ȼ��ȫ�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(l��i)Դ����Q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X(q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I(m��i)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Լ��Z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�ӗ�����ڴ��ﮔ(d��ng)�ĕ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30Ԫ�a(b��)�N���X(q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ϗ��f(shu��)߀��ͦ���õġ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ҬF(xi��n)��߀Ƿ��һǧ��Ԫ�Ă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(m��i)���^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ٚ�һ�^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i���ͣ��i��t�D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ԺÎׂ�(g��)�¡��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⡣
��(du��)��żȻ��(l��i)��һ�ε��L�́�(l��i)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߅����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箋(hu��)���߀�](m��i)����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(du��)�ڗ�Һ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(l��i)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ι�iι��ι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10�c(di��n)��ҲŻ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��ɻ�ɵ����磬Ȼ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µظɻ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ɵ�����10�c(di��n)�Ż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ؼ���ʰ��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ҹ12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˯�X(j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ʳ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^(gu��)�r(n��ng)�v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ܳԵ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f(shu��)��һ�(xi��ng)���صĹ����ǵ�ɽ�_�µĺ�߅��ˮ����"�҂��ĺ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˚q���_(k��i)ʼ��ˮ����ˮͰ���ڱ��t�ﱳ�ρ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һͰˮ�ص��ҿ�Ҫ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С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"
199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ɽ��Ĺ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҂�ס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
1993�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˗l��·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ā�(l��i)�](m��i)Ҋ(ji��n)�^(gu��)��܇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(zh��n)��ɽ�_�µĹ�·�_(k��i)܇(ch��)ҲҪ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߀Ҫ���_(k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С�r(sh��)���x�h������Ļ�܇(ch��)վ���д�s50����ɽ·������ɽ�ϲ�ͨ늣����](m��i)���Ԓ�ȬF(xi��n)���O(sh��)ʩ�������25�q�Ĵ��ĕ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15����ɽ�ºӌ�(du��)���Ĵ��k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g��ɽ�ϵļ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(hu��) 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
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s�J(r��n)�飬������83�q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߀�ǬF(xi��n)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?sh��)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���@Ϣ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Śq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ˠ��堔�^(gu��)�ˎ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ҡ�
"���ɷ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Ҫ?ji��ng)ڄ?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?c��)ڵ������ڄ�����߀��ƽ�΅^(q��)�o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^(gu��)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Ǻ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ʮ���t�Z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߱��t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̫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6�q�����گ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?n��i)��һص��r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](m��i)��ƽ�΅^(q��)���^(gu��)�
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ł�(g��)�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Ѓ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ؑ�����ز�����ރ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"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һ��(g��) (t��ng)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ѽ�(j��ng)�L(zh��ng)��12�q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ɽ�ϝL��(l��i)��һ�Kʯ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"ʯ�^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Ă�(g��)�Ǻ��ڵ���ɻ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С�ރ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ˮ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傀(g��)�t���I���ģ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](m��i)����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еĺ��Ӷ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Ǻ��Լ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](m��i)�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Ͳ���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Ҫ�ɻ"����̫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DҲ���ܲ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S��15�첻�õ�����ɻ����Ļ�߀��Ҫ�ɵģ���
�mȻ����һֱ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߀�Ǹе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һ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@�㲻��ʲôؔ(c��i)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@һ���ٲ�������ؓ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ă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߀���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С�W(xu��)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ă�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傀(g��)�ރ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^̥��ز���ˡ����ČO�ӗ���݄t����ȫ�ҌW(xu��)�v��ߵģ����Ю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Â����](m��i)���^(g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H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F���Ҳ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(xi��ng)l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W(xu��)У�ں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(l��i)��Ҫ���傀(g��)С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߀Ҫ��ˮ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](m��i)�Д[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ˮ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ֻ���ڼ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
���@��֪���ć�(gu��)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�ֻ��"ë��ϯ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ڵć�(gu��)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Ҳ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(ju��)��"�F(xi��n)�ڱȹ����Ǖ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ɴ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Ć�(w��n)�}��"�](m��i)�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"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Ǜ](m��i)�В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H�B�nƱ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Ʊ����һ��ʮ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Î���ǰ�҂��o��ȥ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ֻ�û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߀Ҫ���X(q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"
��֮�����?z��ng)]ȥ�^(gu��)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һ��ǰ����ɽ�µĺ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
��ܑc����ĸ�H����߀�á�"ס�@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ľ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
�ĸ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ĵط�"����һ��ˮ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һ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h�h�L(zh��ng)Ҧ�c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45�ȵ�ɽ�¾Ͳ��m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k��i)��ɽ����С��7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ǃ��N��ֻ�ܼӄ�ˮ����ʧ�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Óؚ��Ψһ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h��110�f(w��n)�˿ڣ�ؚ���˿���32�f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ذ��õ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Щ�˘O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˾����w�M(f��i)���ǧ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(gu��)�ҵķ�ؚ�Y����J���֟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(xi��ng)��"�h����ֻ�п��Լ��I���Y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Ҧ�h�L(zh��ng)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
199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h�O(sh��)����302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100��(g��)ؚ��ɽ���w�Ƶ��^���^ƽ�ĵ^(q��)����"Ч���dz���"����Ҧ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Ȫ�l(xi��ng)һλ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w��߀�Ų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?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hu��n)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?l��i)��ӵ?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ɲ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ĕ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Ҳ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ɽȥ�������Ӆ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҂����H�ݶ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"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"�҂�Ҫ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Ҳ�y������Ǿͺ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"
���⣬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"�҂�?c��)��@��Ҳס�T�ˡ�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ס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
��ԭ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 1996��7���d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A���̕r(sh��)��(b��o)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