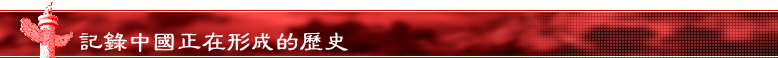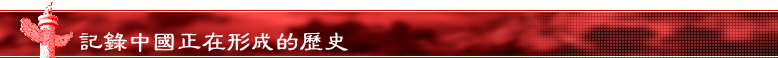|
���ԕ�
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Г���һ���ҕƬ�����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ڕ���ǰ�Ҟ��@�����ҕƬ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}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ˎ������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11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9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|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硢��ɫ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0������Ҳ�֪��ɽ���Č��H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h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Ŀ�е�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Ĺ�s�c��ɣ����һ�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ꐴ��˵ã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_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ɽ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˸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һ���ʵ۽�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Ѩ�ӵ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ʼ���ӵĘ�־����
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˸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Ї��@�ɂ��־ͮ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ǵİ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۴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Ǭ���ɸ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ַքe�ڴ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^21�����ʵ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؝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^59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9����܊����14λ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5λ�Е��ɡ���ë�ɖ|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ᡱ���@�e���o�p����Ҿͳ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A�쌚������˽ܵ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Ľ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֮�P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l(xi��ng)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ǰ�ɱ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쌚���˽ܵ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Ȼ�@��ɽ���˵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@Щ���£�ɽ������ɫ֮�g�Ą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y�c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ɽ���˛]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b�h�ĵ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oɽ����900�|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һ�����ϵĿh�����_�S���ؾͿ��Եõ��L�L����ī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70%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@���е�80%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
�Ŵ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˰��S�೯�������ĸ߷��ﻯ���@��ɽ֮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|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ǰ70%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ʹɽ���ɞ�Ŵ�ˇ�g(sh��)�ĵ��ϲ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r�ڣ��x���x��500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̫�ȿh�IJܼҹ͆T����r�_3700������ܼҴ�Ժ�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ƳɵĻ�܇�^���84.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̫��ĵւ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̫�ȲܼҸ��ɔ�����һ�cҲ�����^�ġ�
�����ς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ʡ�ݡ���ʹ����aɽ�r�����ɽ��Ҳ��ģ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r�ڣ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ԥ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ض��ԕx���_�^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ı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ϵ��Խ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Ї������ṩ����Ҫ֧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^��̫��ɽ�ˡ��ġ�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飬��ij�N�Ƕ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ĸ��_�ŵ����cҲ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Դ�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Ǹĸ��_�ŵĮ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Ŀ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ƽ˷ú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Сƽ�H���ăɂ��Ŀ֮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䓣�������Сƽ��ɽ���˷Q�顰ƽ˷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ƽ˷�Ĺ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@ƽ˷ú�V��һ�ڹ��̰�̫���V���_��֮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@һ���S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1800���h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
̎̎�ǚvʷ��̎̎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̎̎���YԴ����̎̎��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ŵ�֧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|�@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Ǹ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50���g��͢�M��8�δ�Ҏ(gu��)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x�_���r���㰲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IҾ�e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Ż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]�и����z���˵�һ���Ż��ķ�ï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h�M�㲻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С�_ֺ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֞����黱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㱻�Ҷ����У���Ȼ�g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c�@������ij�N(li��n)ϵ���ɽˎ��׃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ꐴ�ζ��Ҳ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ᡱ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ꐴס�����?y��u)���ꐴ�λ�顰���µ�һ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
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Ȼ̫ԭ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Դ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ꐴ���I(y��)Ҳ�M������ꐴ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ꐴ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\������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ζƷ׃�ɱ���Ʒ��׃��ɽ���ɘ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µ�һ�ס��r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ζƿ��s���H�H�Ǿd�������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ᡣ
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Ո��_չ��һ��ӑՓ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һ�ס�߀�����µ�һ�ɽ���ˌ���ꐴķ�ʡ�DŽe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Ҳ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ҕ�����ŵ�ɽ��ʡ��һ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ɫ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ª����ꐴ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H�Ј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ij�h��ؔ�����L��С����ҲҪ���וr������٘I(y��)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ζ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^(q��)��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ˣ�ɽ���˺���Щ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ʡ��ίؓ؟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ϵ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r�f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Մ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Ϻ����V�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ֻ��500����ɽ���s�ƺ����b�h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߀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ʌm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֧�δ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֧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́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l֪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ؔ��(j��ng)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֪����ɽ��Ҳ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vʷ�Ĵ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vʷ��ȥ��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Ї�֮�С�̫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֮�|15�f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ʡ�ĬF(xi��n)�ڕr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ĸ��_�ŵ��@ʮ���꣬Ӌ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ɽ��ʡ�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��Ј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D�y�D(zhu��n)�ۡ����Ї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Ѹ�Ͱ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Щʡ�ݿ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ͬ�r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Դ�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ش�ķ�I�͠������
ɽ��ú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900�|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3.4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2.2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26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΅^(q��)��ֱݠ���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Ж|�����ʯ�Ͷ��ʵ����ͣ���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f�m�^�ڼ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\ú��ʡ�܇���Ӌ���r����ƣ��\���I(y��)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Mʡ�s���Ј����Ƀr��һ�Mһ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ʮ�|�ăr���p����ʧ�s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ĸ��_����ǰ���Ї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ݵ�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1995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y�ˡ�
�����ˠ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ҵ�ؕ�I���@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؛�Ş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ؕ�I�s��ú�c�r���@�N�[�Եķ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˵Č���߀���H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֮�L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ˮ�YԴֻռ�����˾�ˮ�YԴ��4%������ˮ�cú�ǹ����YԴ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y(t��ng)Ӌ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ú��ˮ�����©ˮ���p�ٵ�ˮ�YԴ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�|�����ף�30�f��ˮ����˳ɞ麵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ˮ�r����p�ɞ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ɽ��ɽ�l(xi��ng)��ĸ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ˮ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Ę����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_�RͰ����Щ���̡�
��(j��)�f����ú��ɭ��׃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һ�K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̿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ɭ�ֵ��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ú̿��ʡɽ������һ�K��ľ�Sï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ɭ�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һ�K�S���ء�����һָ̫��ɽ�����̫��ɽ�}�M��ǧʯ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ָ�D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}�M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ʡ�Ӵ�����ƽ��ÿ�꒶����4�|������ɳ�L�L�|ȥ������
ú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ǃ�(y��u)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ú�Į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٪�_�oú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ɹ��I(y��)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٪�_�oú�ѱ��ھ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ʯ̼�����oú�ھ�ɱ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Ľ�(j��ng)���Ƕȿ������ڃr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ô���L����ú˼·�l(f��)չú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ú��ԓ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ǰl(f��)չ�ĺ��m(x��)��֧���a(ch��n)�I(y��)�أ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Դ�ػ������ص�ÿһ��ɽ���˶��o���رܵĆ��}���
ÿһ��ɽ���˶��o���ر�ú��ú�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˲���ק���^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ͬ�Ĵ��Ҳ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֪������ƌ�ʯ���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ú�V��ʮ̎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ԭú��ǧ�f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ǰ�Ĺ�·ÿ��ͨ�^��ú܇��2�f�v�����h�m�����^Ҏ(gu��)���˜�27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ƌ�����ǖ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鳬Խ�Ԅ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֓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µ�һ�ס�ӑՓ��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fҲ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ȥ��6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ǷN�f����ĸ��X�]�˓]�֣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һ�lɽ�X���ٹ�·һһ̫�f·���
�ڱ����e���_��̫�f·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ϣ�ʡί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ۜI����4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S�Z��4��֮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tɫ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υ^(q��)��߀�]����ȫ�[Óؚ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B��ɽ��ʡ߀�]�Љ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)�O(sh��)ʩ߀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Մ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_�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ǧ�f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һ�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r(n��ng)�I(y��)�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)�a(ch��n)�I(y��)�ͻ��A(ch��)�O(sh��)ʩ���O(sh��)��ú���ˮ늡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ɴ�ͻ�ơ�
�@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С�نT�_�Աط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R����s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ʡ֮���M�ԏ����R�Ľk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̫�f·ֻ���@�D���ϵĵ�һ�P��ī�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̫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ľ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ɽ���c�˂������ϵĕr�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5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100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44�����܇������5�f������100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ҹ����144�����̫�f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ҟ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Ԣ�Ա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Ҳ�Ǟ�����һ�l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ɽ���˵�ǧ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80%�ć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Ĺ��º��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f����ס��ǧʯɽ����˼ҏ�ɽ���I���i�б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ʯ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ڣ������挍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h�Ă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(zh��n)�(zh��n)ͨ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l(xi��ng)ͨ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C��܇��̫�f·�����ĵ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��ٹ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
��̫�f·������·�Ĺ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в��չ�_���ĕr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е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20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ɿʵ�ɽ���́��S��֮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֮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Ͷ�Y���^200�|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S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̫�f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ꖳ�늏S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ڵ����ϵ�ͨ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ˮ���µ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չʾ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đ���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Ͷ�Y100���|���Ї�Ŀǰ����늏S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؟�η���һ��32�q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ɽ���˵��ؽ�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ͩ�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4��ȥ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ȫʡ�U���_�ŕ��h��ɽ���˺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Ĉ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g��һ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Еr���Ǿ��^ţ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ׂ��º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˻��Lɽ���r��ɽ���˵��_�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ӿ�������d֮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䁳����r�t�ĵ�̺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ǰ���ɽ��Ͷ�Y�Ĺ�Ĭ��ʿ��ƽ˷��ͣ�Cƺ������
�F(xi��n)�ڹ�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˷ú�V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ˆT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˷ú�V�s��ԭ����̝�p��B(t��i)�D(zhu��n)��ӯ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˷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һ���Ї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_�ģ����cú���\�o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ɽ��ú˼·���D(zhu��n)׃Ҳ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YԴ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Ծ��и���İl(f��)չ�C���Ϳ��ܣ��l(f��)չú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߮a(ch��n)Ʒ�Ŀ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M��ú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ú�Įa(ch��n)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Դ�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ȥ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ܺ����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l(f��)�_�^(q��)�о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ɽ��ú˼·�D(zhu��n)׃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D(zhu��n)׃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һՄ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x�_ú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ܻ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أ��S����ͬ٪�_�oú�Ŀ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Ȫú�V�����R��ȫ��ͣ�a(ch��n)��Խ��Խ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ɽ��ú�c��ú�a(ch��n)�I(y��)���ʎ��ݱ����ĸ�֣������ڱM���̵ܶĕr�g���γ��µ�֧���ͺ��m(x��)�a(ch��n)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ʹ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Ľ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Ãɗl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
�p����·�Ľ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˾���̫�f���ٹ�·���ж��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ٴ��v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ҕƬ���΄ջ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ʹ˽Y(ji��)���c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o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s�ڶ��ٴβ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g���M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Ѫһ���ӷ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ѳɞ��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ҕ����hע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Ū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}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^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ꐴף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@һ�ж���ô��Ϥ���H�С�
�����Ŀ��d��1997��5��21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