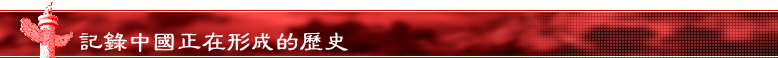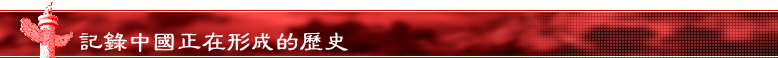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F�˵ij�ؚ����Ҳ���ǻ���ì�ܵĈ�(ji��n)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Ұ�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£��]��һ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һ���ط��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C�،�����Ȼ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ھGɫ�Զ�Č���ƽԭ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ռ�S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r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Ȼ��ì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Ǯ�(d��ng)?sh��)��˺��y�[Ó����ؚ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˵�Խ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Ȼ��ì�ܿ��Կ�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ҕ���յ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ҵ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(d��ng)�ٵ������͖|���^(q��)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ҕ��Ȼ�h(hu��n)���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l(f��)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Ԙ��^��֮��
���L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˲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R�ϵ��`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ܡ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N��߀��ԓ�N�䣬ɳĮ�ܷ��_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h��)�ֵĆ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ؐ�ձ��˻��ƷN��ȵ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댑ƪ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�ǂ��ֵֺܹܹ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ô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l���s�֘O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ȱ���ƌW(xu��)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֪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ݘ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ԓ�^(q��)Ҋ�ڈ�(b��o)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ἰ�����Ć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Ǯ�(d��ng)?sh��)ذ��շ��?y��ng)��(q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ˆT�о���(b��o)�����ж�Փ������@�ɂ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(d��n)�IJ�̫���ھ����ġ�ӛ�¡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c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(n��i)ꑺ�����ɽ�^(q��)ˮԴ���B(y��ng)�ֵ��Ɖģ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ˮԴ���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^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ˮλ�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λ�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ر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غ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֘I(y��)���o(h��)��r�µ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g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࣬��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�}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̶�����̶�ɳ��^(q��)ֲ�����Ɖ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݈��L�ڳ��d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݈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Ժ�m��ɳĮ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ˮ���Y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l(f��)���á���1992����
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ݣ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12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Ğ��ʎX�������ٴ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ˍ{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ˍ{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C�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߅�����Ʋ��^�����Bɽ�����Bɽ������ظ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߅�Ǖr�h(yu��n)�r�����ߵͲ�һ�ı�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ɳĮ�Ͱ͵�����ɳ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ɗlɽϵ֮�g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n��֮�O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ه��(n��i)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ӡ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պӷքe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ĸ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C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G�DZ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B(y��ng)���˾G�ރ�(n��i)���İ��f�˿ڣ�߀��ȫʡ����Ʒ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Г�(d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ٵ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ͻ������ع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K�y�õ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˰��Ә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B(t��i)�@һ�Ƕ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䌍(sh��)��һ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]���S����ԭһ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е��S���Ӻ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ݾ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?sh��)ذ���ֻ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ϴĘϴ�³���طN�f�ڣ����Զ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ǰ�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С��ˮ���S̎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һ�l��һ�l���СС���L�L�̶̵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Ϥ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ӡ����պ����lˮϵ������lˮϵ��ȫ��Դ�����Bɽ������ς�(c��)���Bɽ�ϵij���eѩ�ͱ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Ǫ�(d��)�ض��Q�ǃ�(y��u)Խ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Q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r(n��ng)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I(y��)�l(f��)չҎ(gu��)ģ���Q�ǃ�(y��u)Խ�Ě���l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Ͽ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꽵������180m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t���^2000mm����жΏ�Ҵ���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30m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ӽ�2100m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ÿ�꽵��30-60m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Օ�sʹ�˵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3000-3500m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�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ǹ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1000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f�ڹ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ïʢ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μ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ɽ�ϵı�ѩ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ȡˮ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¾�ˮ��Դ�^Ҳ�����B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˼�h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Σ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20�f�˾۾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;�Ȫ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�ˮԴ�������Bɽ�ı����ͷeѩ��
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h(hu��n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ȁ��f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G�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к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Ƭ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ɳ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ṩ�n��֮���ٟo���õ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l(f��)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đQ�Ļ�Į�����ء��@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G�o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ں������ȵ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hu��n)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ܳ����e��һ�����Bɽ�@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Ɖ�����ɽ�ϵ�ˮԴ���B(y��ng)�ֱ�횵õ����ƶ���Ч�ı��o(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ƌW(xu��)����ˮ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ǃ�(n��i)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һ���ƌW(xu��)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dz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һƬ�֣�ɽ��(sh��)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φ̺࣬����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ֻ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B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BɽˮԴ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e�p�����ѩñ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ɽ���B(t��i)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n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˓�(d��n)�n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ɽ�^(q��)�ֵ������Ɖ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I(y��)��ɽ���֘I(y��)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ɽ��Ȼ���o(h��)�^(q��)��Ŀǰ�������o(h��)�^(q��)��(n��i)�r(n��ng)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D�ֵ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h��)�^(q��)��(n��i)�˿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h�˿ڲ���7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ڸ��_(d��)20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ɽ���B(t��i)�h(hu��n)��ѩ����˪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Cʡ�֘I(y��)�d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ʿ��ӳ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ڱ��o(h��)�^(q��)��(n��i)�y���y���ͱI����ľ�ĬF(xi��n)��߀�Ǻ��y�Ž^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ߴ���F(t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ˆT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Bɽ�^(q��)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ֱ�Ӻ��֮һ���dz�ɽ�ڵ�ˮ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Ժ�m�ݷ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Ĕ�(sh��)���@ʾ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A�����Bɽ��ɽ�ڵĿ�ˮ����69��7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15��9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36��8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պ�17��2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(sh��)�ֱ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ˮ���Ĝp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ή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ǰ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ή�s�ľG�ޣ�ÿһ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֧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֘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֘I(y��)�о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ȫ��ʿ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^���_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ˮ���YԴ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^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ǚ��uȡ�ѡ����Fֹ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ȿ����أ���ʯ��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�e��24�����55�f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93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_(d��)28������60�f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ؓ(f��)�d��e4����05�f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˿ڣ���(j��)(li��n)�χ�1997��Mӆ�Ę�(bi��o)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ɺ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،��˿ڵij��d���O����7��/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15�����8��/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ǰ�˿�߀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ڜp������1978��199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9���41%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24��01%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35������97%�����˵��峯���еġ��˝M�p֮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Ժ�m��ɳĮ�о���1992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ˮ���Y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l(f��)���á�¶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݈�Ŀǰ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݈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ʮ�և�(y��n)�أ��݈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^(q��)�݈��˻�800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˻��݈����^40%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Cʡ��ɳ�о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Գ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һƽ������IJ݈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ֻ���҂��@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Ӌ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ĺ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��Ȼ���B(t��i)�ஔ(d��ng)����ĵ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xˮԴ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ֱ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һ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淽ʽ�c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H�ߵ����ھ��ǬF(xi��n)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^ȥ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F�Լ��F�O֮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汻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փɴ�ɳ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ڱ�ɳĮ�ͻ�Įһ�c(di��n)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ȱˮ�������ȱˮ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λ��ʯ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ĵ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S�Ĕ�(sh��)Ŀ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ȻҲ��ö���ȥ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ĵ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n�����Nֲ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̫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ږ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ή�s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ֱ�ӵ�ԭ����ʯ��Ӂ�ˮ̫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ڿhί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��Y���@ʾ����40�����9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õ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ˮ����ÿ10��1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ٶȜ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0�����6��5�|������/�������90�����1����2�|������/�ꡪ��50���g�p����5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β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ξʹ�������7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0���g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11000���ۣ�300�����25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_�ɵ���ˮ6��5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(d��ng)?sh��)غ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8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ˮλ�����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ˮ�o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ͬ�r���ڹ����ˮ���㣬�����ε�ˮ�|(zh��)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}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70����ԁ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}�n��2�f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һ�M(j��n)���ھ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R�ϸ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ˮ�YԴ�İ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ֺ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|߅��һ���r�[�r�F(xi��n)�Ľ�ɫ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е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ɳĮ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(c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ƈ�Ӛ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@�۵ģ���һƬƬ��?y��n)�N�Nԭ��U���Ļ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؏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ǯ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ڿh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Ļĵ�Խ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ҲԽ��Խ���ʮ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һƬ��Ұ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܇���Ұ����һ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Ԫ�����һ�M���S�_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һ�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S�_܊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Ҳ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]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�M��ľ���6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ľ�ˮ�B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_܊�f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9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Ո�폈Ҵ��ˮ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̽�xַ���ټ��Y���һ����1000Ԫ��һ���M����24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0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߂��M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һ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ˮ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ϵؾ��ǰ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�Ķ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һ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£��S�_܊�f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˕���߀�ܶ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ھ�ֻ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߀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ׂ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ȥ30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�߀�ǿ�ˮ��ֻ�õ���Ԫ�@߅�I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K�Xһ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ڣ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ǧ���f����ë֮�ض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_܊�ҵ�ʮ�����㲻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Ԫ����Ļ�Ұ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ɳ�P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o������Ӱ�͟o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·���� �õ�ɳĮ�Q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͕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@ô���v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뻢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ڵĿsӰ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sӰ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ص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ɞ�������ȵĿsӰ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ϵ200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顰�Ϸ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ʮ����Ѯ��